一家媒体报道说,在东北,大学生毕业后最大的人生规划就是“吃上公家饭”。有人考了9次公务员,有人花了大钱“打通关系”,有人放弃民企的高薪,有人争破头只为一个扫大街的事业编制。他们坚信,“没有编制,你什么也不是”。
看到这则新闻(下方有原文),唏嘘之余,隐约看到“年轻人该不该去体制内”的困惑。然而,当“体制”和区域发展关联在一起,问题就变得不简单了。
如果说对于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年轻人来说,到什么性质的单位工作,关系到个人价值观、发展定位的自由选择的话,那么东北年轻人的选择区间可能很狭窄。
在哈工大举办的一场招聘会上,大部分参会私营企业来自外地,如果不离开家乡,毕业生还有不一样的选择吗?
市场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不健全,去留体制内就是个伪命题。
谁都有权追求舒适的环境,现实中,如果一份“体制内工作”给人充分的保障感、提供体面的生活,而“体制外”看不到远大的前景,就别怪求职者“趋利避害”。
在创投领域,有一个常用名词叫“试错成本”。在“编制”成为香饽饽的地方,年轻人的试错成本往往更高。
江浙沪的淘宝青年可以不停尝试新的产品,创造新的需求,直到成功与市场对接,但在东北,错过编制可能意味着错过很多机会,放弃编制又意味着独自面对未知的未来。
编制给人以安全感,归根结底还在于市场不够强大,不足以在一次失败以后,为年轻人缓解社会和周边的压力,提供更多的尝试机会。

其实,东北人并不懒,一旦有适合自身的新业态,他们也会抓住机遇,趁势追击。比如,网络主播就有很多东北人,说东北人占领直播业半壁江山并不为过。不过,网络直播终究是特殊的业态,它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因此也不会“水土不服”。
人们更关心的是:更多的实体民营经济能否在东北落地生根?东北能否搭上轰轰烈烈的创投热潮的班车?
众所周知,北京、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传统上创业的“三极”,但近年来诸如成都、贵阳、郑州等中西部地区,也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创新型产业。东北区位条件并不差,岂能在这场竞争中落伍?
与东北青年在本地求职追求编制相对照的是,迁徙到外地的东北年轻人,展示出强劲的活力和潜力。很多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都能看到东北人奋斗的身影,以至于给人造成了东北年轻人流失的错觉。
据国家发改委的调研,东北地区并不是人口净流出最突出的地区。不过,有一个猜想值得更细致的观察——
东北最优秀的年轻人去了哪里?他们是留在本地守着一份编制,还是更愿意到外面闯一闯?

当稳定的编制内工作成为一种集体追求,还可能导致“吃螃蟹者”成为异类。“既得利益者”能不能脱离自身利益格局,为变革让出一点空间,才是推陈出新的关键。
与其抱怨体制,不如改变人的因素,人变了,体制自然会朝更好的方向前行。如果每个人都沿着僵化的路线,发展格局就可能越来越板结。
追求编制,本身并没有错,一个环境让编制成为最好的甚至唯一的选择,才是问题。
东北要有更大的胸怀,容纳下年轻人的理想和抱负。期待这片原本肥沃的土地重现生机。
相关新闻:《东北青年们的入职选择》
部分年轻的东北人离开校园后,有人考了9次公务员,有人花了大钱“打通关系”,有人放弃民企的高薪,有人争破头只为一个扫大街的事业编。他们相信“面试一定要找人”、“私企都容易倒”,他们毕业后最大的人生规划就是“吃上公家饭”。因为,“没有编制,你什么都不是”。
在得知自己被天津市某区交通局录取的消息后,性格内向、被朋友看来甚至有点木讷的吴天君在QQ动态上写道,“自己的世界终于又打开了一道口子,阳光重回大地。”
从2009年大学毕业后,吴天君共参加了9次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笔试、面试。
其中,为了能通过老家吉林省抚松县的一家事业单位面试,他的父亲动用家庭的存款和向“铁哥们”借款等方式共筹得20万来试图“打通”关系,但也以失败告终。
为进入“体制”,吴天君的邻居张静,在拿到辽宁省某师范院校硕士毕业证书5个月后则选择继续等待。

执着于进入体制的,并不只有东北人。图为江苏省公务员考试前,一名考生举着准考证进入考场。
政治学专业出身的她把这5个月来找工作以及实习经历戏谑为霍布斯式的“战争状态”——“霍布斯总结,人类的初始人性中会因为三件事情而进入战争状态:得利、安全以及名誉。”
这场进入体制内的“闯关游戏”,竞争者就像一个个争夺城墙上那支鲜红的旗帜的战士,只有踏着敌人的尸体,几个手持旗帜的人才是胜利者。
2016年12月26日,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布了《2016年投资环境指数报告》,粤苏鲁浙闽位居投资环境前五位,而东北地区是四大板块中投资环境最差的一个。
投资环境落后的十个地区中,东三省占了两席,黑龙江则排倒数第一。
一项针对我国七大地区营商环境的调查显示,在2001-2011年期间,曾在东北开展投资或有实际经营的外地企业中,有66.4%的企业“已停止在东北地区经营”或“在未来5年内有离开意愿”。
随着东北经济的停滞与民营经济的不振,留给东北年轻人的选择并不多。除了到外地寻找机会以外,吃“公家饭”便成了很多年轻人的人生规划。

2016年7月2日,辽宁沈阳,一公务员考试面试考点外排起长龙。
“没有编制,你什么都不是”
“想做这一行,先准备20万”
关于父母对自己进入“体制”的期望,张静提高自己的音量说出四个字:“相当建议”。张静的父母在吉林抚松县的泉阳镇国有农场里承包土地,种人参。
但随着这几年价格下跌及假人参对市场的冲击,张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如前。近几年,她的家人和亲戚去往东北经济较好的大连寻求工作机会。
相对于农场收入的不稳定性,“父母希望我能成为教师或者公务员,有个稳定的工作,不用为失业下岗啥的担心。”
2016年11月的“国考”报名,张静选择了沈阳海关办公综合岗位,367人报名,招录2人。“实话说没有底,有种为了报考而报考,我还是把希望寄托在2017年春季省考。”
而即使是竞争相对较小的吉林省省考,2016年的公务员考试人数也再创新高,报考总人数达到5789人。
张静两次被“善意提醒”需要找关系。
“在前往大连甘井子区(教师招考)报名现场,一个教育局内部的阿姨跟我说,如果你笔试过了,面试一定、一定要找人。”
更早时候,在2009年高中毕业前的一节政治课上,老师在课堂上直接聊到,如果想在大连经济开发区高中当老师的话,你得准备20万元,“20万非常值。”张静还记得当时政治老师说话时带着一种不容分辩的表情。
张静的男友,正在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的刘建林对她进入“体制”的目标表示理解,在老家辽宁鞍山海城一个偏远乡村多年的生活经验告诉他,“没有编制,你什么都不是。”
刘建林是村里走出去的第一位博士生。在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村邻们对他家表示了短暂的敬意和礼貌。但因父亲的一次意外受伤,他发现,“在乡下,没有关系,你就是被欺负的命。”
刘的父亲没有正式工作,常年做建筑工地小工,只有9月农忙时才在家收玉米。2015年冬天,刘的父亲在邻居家的自建房楼顶砌砖时不慎摔下,左脚粉碎性骨折。在海城市医院和鞍山市动手术和休养的这近半年时间,花费了近2万块钱。刘建林希望那家雇主能进行赔偿,但遭到拒绝。
无奈之下,他把雇主告上了法院,最后判决也是民事调解。“开庭前,律师提出治疗费和误工费10万元的请求,但最后他连一分钱都还是不给。”刘建林很是无奈,“私下协商,他不拿,你完全没办法。”“要想改变命运,我只有希望自己进入大学任教这条路,让自己身板硬起来。”他说道。
只要有实权,副科级也受尊敬
在等待和准备公考的日子里,张静在某教育培训机构做面试助教,在没有单独排课的情况下,公司没有提供合同、零薪水,“当模拟面试老师的助理,我可以学习面试技巧,平时还有时间备考。”
随着“公考”临近,培训机构的工作量加大,张静经常早上6点起来,花一个小时去单位,晚上7点才能下班,“挺遭罪的,大冬天还冷。”据多家媒体报道,如今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产值保守估计在十多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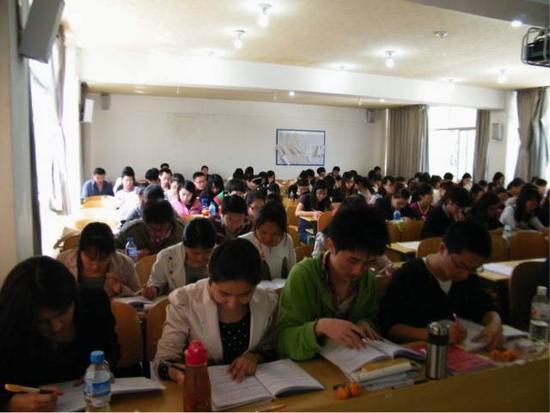
忙于备考的学生
主营出国留学考试培训的新东方,也在2006年创立了公务员考试培训中心。2016年6月刚毕业那会儿,大连文都教育集团给张静提供了考研政治老师的工作机会,但还是被她拒绝了,理由是学校的商业气息太重。
26岁的张静和男朋友刘建林展望未来的生活。刘建林正努力读完博士后留在大学任教。在三次教师招考、一次省考失败之后,张静也并没有打算放弃,即使她现在只能借住在刘建林的博士宿舍里,“等到他也毕业,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家。”
一位不愿具名的市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在实权部门,他尽管只是一名普通的副科级,但找他办事的人接连不断,且态度礼貌和蔼,“平时,东北大爷估计没两句就开始说粗话了”。
“体制内的工作稳定、受人尊敬,那么多人挤破头想要进来也是理所应当的。”上述市政工作人员说道。
放弃百度高薪职位
有编制扫大街也行
宋纯政的老家在哈尔滨东边的一个郊县,距离市中心有100多公里。
有时候,结束市政府“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安排后,周末,他还会回老家帮忙照看母亲的水果摊点。“冬天,你在哈尔滨室外摆摊一整天,全身都是麻的。”他对各种水果蔬菜的品种和质量了然于心,在与供货商的通话中头头是道。
作为一个普通铁路工人的孩子,现在所有邻居都知道他在市政府上班。如今,他在哈尔滨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做着掌管“铁饭碗”的工作,而单位里还有好些没有编制的同事也在做着和编制问题挂钩的工作。
宋纯政52岁的父亲做了一辈子的铁路一线职工,在铁路工务段的老宋负责铁路路轨、铁路线路改造和维护维修的工作。
在行将退休的年纪知道自己的儿子每天坐着市政府的接驳车上下班,“我挺为自己儿子的工作感到自豪。坐办公室,他不用再像我这么辛苦了。”宋的父亲说道。
老宋说自己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国家的铁路事业,对于儿子的工作,他认为是一种传承,“现在,我把儿子也交给了国家。”
宋纯政本有机会在哈尔滨百度公司工作,拥有现在两倍的薪水。“百度哈尔滨公司类似于营销和推广的企业,薪水高一点,但总觉得不稳定,兴许哪一天工作就黄了。我毕业前获得政府工作机会,这是我和我爸都接受的第一选择。”
2012年11月,在宋纯政大四那年,关于哈尔滨招有“事业编制环卫工”的新闻热炒网络。
哈尔滨市招聘457个清洁工引来1万余人报名,其中近三千人拥有本科学历,25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事业编制”是他们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宋纯政的本科同学刘文也报考了这个“事业编环卫工”职位,但最后也落选了,只能在社区当服务人员。“我能考上扫五年大街也比现在强吧?”

被分派到哈尔滨南岗区城管局保洁一大队的两名研究生(中、右)在巡街保洁时过马路。
几年来,刘文没能考入体制内,他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之前我爸还开玩笑,如果你找不到工作,就去扫大街啊。”
张静回忆,连自己在国有农场里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也认为,拿到硕士文凭就是知识分子,扫大街不是目不识丁的人干的活吗?“但在编制面前,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东北的毕业生招聘会上
国企挤满人,私企打酱油
在哈工大2017届毕业生秋季大型招聘会上,根据我们统计:
11月18日的全部448家参会单位中,驻地在东北的仅有93家,其余的都是东北外的企事业单位,且大部分参会的私营企业都是外地的。
这意味着,哈工大学生想要在招聘会上选择私企,很可能需要离开东北。

在哈工大举行的东北五校大型招聘会上,人生人海的应届毕业生。
主营塑胶和电池的厦门天力进出口有限公司是448家参加招聘会的企业之一,当时在东北去了哈工大和哈尔滨工程学院的招聘会。
其负责人张夏清表示,因为公司是人才中心的合作企业,公司会通过厦门人才中心提供的地区、学校表单推荐,再决定去不去现场招聘。
“招聘现场好企业还是很多,很多国企都是挤满了人,我们几乎是打酱油的。(学生)感觉私企都容易倒掉,其实我们是有信心的,但别人就不这么看。”
作为东北地区最知名、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吉林大学某学院学生办公室负责人向我们提供了两届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表,选择在“体制”外发展的毕业生远远低于进入“体制”的人数。
每届140位学生中分别仅有6人和13人入职了民营企业,“其中有5个学生是苏宁电器的特招生。”该负责人表示。
吉林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中心管理科科长鲁凯认为,进入“体制”一直是全国普遍现象,东北地区民营经济的弱势也间接造成其热度常年不减。

东北五校大型招聘会上的求职者。
据该中心发布的《吉林大学2015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2015届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单位流向中,37.57%选择进入国企。
而同年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进入国企的本科毕业生比例则分别为19.25%、20.74%、27.28%、11.56%。
针对上述情况,吉林省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郑志宏表示,吉林大学等东北高校的就业情况是东北地区的普遍缩影——“相对于发达地区,民营企业薪水低、岗位少。”
“就国有企业而言,虽然建国以来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普遍采取了单位制,但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空间条件,使得单位体制的诸要素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出现得最早,贯彻得最为彻底,持续时间最长。”长期研究东北国企问题的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田毅鹏教授说道。
最后的油田子弟:
“离开大庆的人没有责任感”
27岁的赵明自称是大庆“最后的子弟”——这意味着,在哈尔滨某“二本”、“三本”毕业的他们是大庆油田最后一批非考核而进入油田系统的大庆青年。
“在这之后,想要入职的毕业生全部靠公开招聘,油田子女这条杆也不好使了。”赵明提到。

当年从哈尔滨理工大学毕业后,赵明被直接分配到操作岗位,成为一线采油工人。入职三年后,赵明通过内部的审核考试成为一名矿区会计,晋级管理岗。
大庆278万常住人口中,至少一半人和赵明一样,从事与石油相关的工作。2015年,大庆市GDP30年来首次负增长,下降了2.3%。
即便如此,赵明对那些选择离开大庆的年轻人表示不解,“没留在大庆的人,就是不值得留在大庆的。没油了反而跑了,这不是没有建设大庆的意思嘛!”他激动地说。“比如动乱了,有人会首先逃跑。但是遇到危险,我会拿起枪,保卫我身边的人。特别优秀不回来,因为他(对大庆)没有责任感,个人主义。”
即使油田子女的“铁饭碗”被打破了,但赵明还是希望有一天能恢复。“现在不是因为政策错了,是因为我们经济条件实行不下去了,养不起那么多人。我们在厂矿成长起来的就应该照顾,他们最应该回到这里工作。”
已经开始坐办公室的赵明有时候也会怀念在矿井的生活,“一大早在空地上开个会、喊个话,一起骑车去工地,然后中午一起回食堂,跟大锅饭似的,菜也做得很好吃。热热闹闹,人不可能离开群体嘛。”
“观念这种东西,一旦适应后你很难去改变它,就好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那个叫布鲁克斯的老头,出狱后就自杀了。”赵明说。
网友评论
@pink:
我是南方人在东北上大学,大一的时候如果看这篇文章绝对没有现在有感触。
别说东北经济和社会风气,就是这种“编制”这种关系风气在一个大学里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学生干部竞选、寝室调动,都需要那“二十万”!
东北至少比其他地方更突出“人情”色彩,现在的感觉就是念完四年赶紧逃离这个压抑的气氛!
@段凯华:
可悲!
七年前,从东北来到广东。
从职场小白到拥有一技之长,而立之年,期待未来大展拳脚。
我觉得,离乡背井确实不容易,但却总会有期待,而反观东北,实在心凉。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选择离开。
@安静静闭关修炼:
土生土长在东北,真的觉得很压抑,将来很想离开家乡去外地打拼,可是家里就是想我回去,说嫁个好丈夫就行了。
不懂,那我苦学这么多年的意义在哪呢?
何况,留在家乡的东北爷们除了喝酒打架的血性,已经没什么拼劲了,很可悲啊……
@一朵朵朵朵儿:
我自己也是东北人。对本文所揭示的现象表示认同。
东北很少有民营企业,投资环境差,除了公务员和事业编根本没有别的选择了。
而且走后门拖关系风气严重,感觉不花钱根本找不到工作。
我自己今天top2硕士毕业,很顺利在北京找到了工作。
家里这边的熟人听说以后,第一反应就是:花多少钱安排的?我父母说没花钱,他们都不信。
东北就这样的风气,能留住什么人才?有什么发展?
@博:
作为一名来自广东的大学生,我能说我在家里观察到的结果是公务员是受人歧视的吗?(弱弱地吐一句)
我爸天天就对我说,你要是不努力就只能像XX的儿子(女儿)一样去当公务员,没出息。天天看别人脸色,工资还低。。。。。。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样,但是在我的交际圈里对公务员不是冷漠(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就是歧视(比如我爸),导致我刚来北方读大学的时候价值观受到了极大冲击。
@企鵝不會飛嘿:
在东北有一种很无奈的感觉,即使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国企,也会生活的比较迷茫。
我作为从华东回来的教育部重点大学的学生,说实话是后悔的。
整个东北不仅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没‘关系’什么都别谈”,并且经商环境和政府部门管理极差。
在这里的民企大多都不够规范,因为一旦规范起来政府部门给的压力几乎可以使其倒闭。
国企则畅通无阻,大连这样的代表都大有衰退之势,更别提其他城市。
政府推诿扯皮和暗示你拿钱的时候非常多,似乎大家都抓住体制和计划经济时代尾巴如同救命稻草,拼命刨出最后的利益榨干东北的价值。
很可悲,坠落就是一瞬间,却积重难返。

